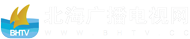【讲好中国故事】我才是大海年轻力壮的儿子——北海疍家风情录
发布时间:2023-12-11 20:59:06.0来源: 
海上“浮城”。
(一)
想起北海侨港归来的渔船与渔船一只只靠在一起,尤其是依偎在它们住家船的身旁,仿佛就长出了双腿站在海湾里,长出了一种山的巍峨,长出了一座海上浩浩荡荡的浮城。
它也让我想起那位绰号叫光头四的北海疍家子。跟我接触到的喜欢嘻哈打笑的年轻渔民不一样,他的表情总显得有些凝重,眼神里含有文人气的恍惚和举棋不定,尤其是坐在铺有红蓝条纹塑料编织布的船舱里的时候,暗光中的他甚至显得有几分忧郁。
记得那是个无比闷热的下午,雷声在低矮又厚实的云层里偶尔吼上几声,正在冲洗捕鱼船的光头五压着嗓对我说:四哥想阿荔了。阿荔跟着一个来北海做生意的外地仔走了。这年头,有些脑袋进水的疍家妹开始嫌弃我们这些漂来漂去的海上男人。却不知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重庆市散文学会副会长,2002年获重庆首届散文文学奖,2003年获重庆文学艺术奖,《与谁共赴结局》获2004年重庆散文十年作品经典奖。小说代表作《男根山》。
那些外地仔是满世界在漂,谁更不可靠!听到这些话的光头四,霎地从船舱里窜出来,把一瓶矿泉水狠狠掷向五弟,骂:胡说个什么八道……

接驳渔获。
(二)
光头五当年说的“这年头”是1993年。那一年各种外地口音像回南天的湿雾在北海四处弥漫,肯定也飘去了像他们这样停泊在海洋与大陆间的渔船。只有高中学历的光头四就是那一年爱上写诗的——因为阿荔,因为他像鸡蛋一样随时都会粉身碎骨的爱情。那个叫阿荔的疍家妹我见过,有着令人一眼就迷上的漂亮,大眼睛大胸脯,盘着腿坐在船头织渔网,投到水里的影子也会招来一群群的鱼虾。光头四曾为她献上这样的情诗:我相信凭着年轻的肌肉和臂膀/会闯过大海里所有的深渊与火焰/陷我于灾难的/只有你阴晴变幻的双眸/不让我靠近的嘴唇……
1993年的这个夏天,光头四遭遇着堪比海难的情感浩劫。它其实是有先兆的,否则,他不会突然像抓一根稻草似的去抓住诗,像拽住一位亲人似的拽住我这个他觉得能懂他诗歌的人。
因为诗,他把我这个“番鬼婆”真当作了自家的大姐,隔三差五,便会为我拎来一篼昂贵的石斑鱼或象鼻螺。还会脸一红,紧紧张张塞给我一支卷成细筒的信笺纸,嘿嘿地笑着不说话。那又是几首他新写的诗。他写道:“大海啊/把最不苦涩的那朵浪花赐给我吧/我会手持永不熄灭的渔灯/在离涠洲十海里的无人岛/和她举行婚礼”“谁也不知海的拥抱比女人更温暖/它日复一日喂我食物/赠我战袍和战马/以及/从不相同和平庸的天空和诗行”……隔着肌肤、肌肉,他的诗也会直接把我的灵魂烙痛。我体会到真正的诗歌,永远是人汗流浃背向着海洋、土地讨生活,或欲生欲死爱一个人时迸溅而出的,绝不是百无聊赖、虚情假意、打情骂俏日子里挤出来的。光头四与诗歌的距离比我们都近。
1993年对所有疍家人,甚至北海所有的本地居民都是大起大落、充满挑战的一年。有大半年,光头四仿佛人间蒸发。有人说他是带着五弟跑到湖南寻阿荔和带走她的外地仔了——啥时代了,疍家再不是贱民,他要和外地仔来一次面对面的、公平的“交流”,更想亲耳听到阿荔说出弃他而去的原因;有人说光头四是驾船奔去了深圳、香港或更远的澳洲。他要去找大钱回来娶更靓的妹仔。然而某个夜晚,光头四却忽然轰轰开着摩托车来,什么都不解释,只说带我去“听船”。而我也什么都不问,毫不犹豫跨上摩托随他去了。
所谓“听船”,其实就是坐在侨港的石堤上,面对脚下成千上万密密匝匝挤在一起的船只,听它们的动静。可以说,眼前这座壮阔的、望不到边的浮城,让我好生惊讶与震撼:它们是什么时候诞生的,又是什么带来的,难道是黑夜、潮汐与月亮吗——
近处的船上有女人踮着脚在往高处的竹竿上挂渔灯。光头四便指着说,那是住家船,一直停在那里的。看着它怕有五六米长,够大,可能会住上一家三代的。果然,便听到船上有老人咳嗽声、孩子的打闹声,女人尖着嗓在吵吵嚷嚷的声音;“你看,那可能是小夫妻船……要不哪会这么早就把船舱帘放下了……”果然,那儿黑灯瞎火,唯有整条船在随着潮汐的进退摇晃。
除了这些烟火气的声响,这里也有各款音乐的交杂撞击:坐在船头的老阿公抽着水烟,用收音机听着“红线女”;摇着贩货船过来的妹仔却唱着孟庭苇的“每当天空又下起了雨,风中有朵雨做的云……”她的桨声和歌声像一把铁桦树木做的犁耙,把水翻了个遍并弄碎,水从刚才的酱紫变成了轻松的湖蓝。
此时布满繁星的夜空仿佛探着身子倾斜下来,发出了不可名状的吮吸声,浮城也微微摇晃了一下,接下去是更加牢固的壮阔、望不到边,以及深邃的神秘。
我说:“我喜欢它!”光头四沉默顷刻,说:“我也是。我哪里都不会去。”
回到家,读光头四新写的诗,彻夜不眠!他在和谁叫板啊?“从不以为我是陆地的弃儿,我有御风而行的自由,所有海洋的生物都是为我而骄傲的兄弟,站在身后,大声歌唱……”这样的诗,让我有了一种很强烈的念头,想去了解那个被称为疍家的族群。

水上人家。
(三)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,疍家人生活逐步有了改善,也有了一些疍家人迁徙上岸,在陆地上修房居住……但,血液里他们仍是习惯海上生活,就像那些习惯流浪的吉卜赛人一样,动荡的日子被他们当成那种喜欢咬在嘴里、咬出一嘴血红的槟榔。它很是苦涩。但一块块细细去嚼,“脸颊渐渐发红发热,身上慢慢就有了暖意”,在海上的御寒抗风湿,它是最良善的药。
我终于理解了光头四为何有时会有气吞山河的笑,那笑声几乎要把太阳都掀下来似的;有时却又蜷缩在船舱里,一动不动,一声不吭。他恐怕是在如此起伏跌宕的情绪中来质疑、确认自己是谁,来自于哪里,以此来疏通肉体与灵魂间的那道桥梁,并追问自己该去向何方,难道上岸便是他们这个族群最好的归宿和最后的胜利?22岁的光头四坐在海堤上,千百遍去听黑夜间浮城的喧哗以及寂静后人们发出的梦呓,又会因迷茫而诗兴大发:我叩响你的门/大海/请给我哪怕一缝隙的光……
我是在离开北海前去了光头四一大家子的住家船。那里算是他们的母船,也相当于我们陆地人的老家。船有六米多长,接近3米宽。不知为何它让我联想到《圣经》中的诺亚方舟,那座传说中帮助人类渡过滔天洪水的避难所。而这种表述仿佛还不准确。无比触动我的还不仅仅在于它提供给了这家人所需的遮风避雨、起居休息的空间,更在于它就是那么丰盈而温馨的家的存在:船板、船舷抑或整条船可能都经常用桐油细细刷过,才会在玫瑰色的暮色里,闪烁着让人感到亲切的光亮;舱里虽无陆上人家的桌椅床榻,但每一角落都毫无纤尘;靛蓝色的布帘图案不俗,有数不清矫健的蝴蝶穿行在花枝间。对,矫健,我想用这个词来送给光头四的所有家人,从他的阿公阿婆到14岁叫阿岘的小妹妹。他阿公盘着腿坐在那里还让人不觉得,一站起身,吓我一跳——他怎么都在一米八以上,清瘦,海塔似的挺拔。
光头四在想什么?月明星稀下的他,被来自天上与海洋间突然放射出的耀眼的光镀了一层银色,也像是被什么灌醉了似的,嘴里嘟囔着,张开双臂,从海堤这头跑到那头,像要去翻江倒海的大白鲨。终于,他折腾够了,一屁股坐下来说:姐,信不信,我会发财的!绝对会!不到10年我就会把住家船换条更大的!我还会在北海最靓的高处,修一幢白光光的小洋楼,通通种上仙人掌和曼陀罗……我就是个贪心的王,不但要在海上看日出,还要在白房子前看日落……

疍家婚礼。
(四)
前年我重返北海,不敢想,已过去21年。嗅到北海第一缕阳光的时候,涌出的念头竟是,那个疍家仔的光头四还写诗吗?
北海的冬天爽朗而娇媚,尤其是不刮海风的时候,吹来的再不是春夏那种黏黏糊糊湿兮兮或热烘烘的东西。一丛丛的三角梅像气场十足的女王,用高饱和度的玫红或艳紫让这座城一年到头也见不着衰。
更让我惊喜的是各种疍家风情、疍家元素扑面而来。朋友首先在外沙桥的疍家酒楼为我们接风,而后又带我们去逛了逛银滩的疍家小镇。正遇镇上一群疍家大妈在与男人们对歌。六七十岁的光景了,却个个活得新鲜,穿粉着绿的,嘴唇抹得鲜红。从这条凳跳上那条凳时,气都不喘一口,歌声照旧炸街。又让我想起了那个形容词:矫健。
我却无法找到光头四,北海也成了我不开导航根本就找不到任何过去的故地。从某种意义上讲,一座很轻易就让人迷失的城,也到了不仅需要诗,更亟须大部头的长篇小说、多结构的交响乐曲来呈现其恢宏、复杂、多元性的时候……只是怎么也忘不了北海曾给予的诗歌,那些具有浓郁的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特质的诗歌。所以,每游一渔村,看到某幢立在高处,专心致志凝望着大海的白色小楼,都会生出莫名的兴奋,拉着同行者嚷道:看看看,那幢白房子肯定是我朋友的;看看看,那些仙人掌和曼陀罗肯定是他种的。他这样写过:带你们一道去看海的酣睡和苏醒/扎破手心的仙人掌,低头不说话的曼陀罗/左边是我的妻子,右边是我的妹妹……
(本版配图均为徐绍荣摄)

作者简介: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重庆市散文学会副会长,2002年获重庆首届散文文学奖,2003年获重庆文学艺术奖,《与谁共赴结局》获2004年重庆散文十年作品经典奖。小说代表作《男根山》。
来源:北海日报